发表于:2021-03-29

马克思指出:“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化身”。苏格拉底毕生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奠定了哲学的基础,指明了哲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表明了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爱欲哲学——“爱智慧”的学问。
哲学既然是一种“爱智慧”的爱欲哲学,必然要涉及爱欲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涉及“爱智慧”的主体为谁、所爱之智慧若何以及主体如何去爱智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在柏拉图眼中,这个爱智慧的主体不可能是身体,只能是灵魂;而所爱之智慧,不可能是具象的身体或形体之美,只能是自体自根的“纯美”“纯善”,即美的理念和善的理念本身;主体追求智慧的方法和手段不可能是感性直观,而只能是理性直观和理性分析。正因为哲学本身不是智慧,它自诞生之日起就“缺少”智慧,哲学之魂——无论它是灵魂、意识、自我、精神还是主体——才会如此强烈地去“爱智慧”,即爱理念和关于理念的知识。
柏拉图对哲学性质的这种规定,对后世哲学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自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把爱若斯解释为灵魂渴望与它所没有的东西合为一体开始,西方思想似乎注定要把人类经验明确表达为欲望对象的“缺乏”并努力克服这种“缺乏”。这种哲学倾向,就是“自柏拉图以后,哲学主要不是讲人与存在的‘契合’或‘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而是把存在当作人所渴望的一种外在之物来加以追求的东西”。

柏拉图之后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无一例外地从两个方面继承了柏拉图的爱欲观:其一,严格遵循柏拉图把欲望二分成理性欲望与身体欲望的这种区分,推崇理性欲望而贬低身体欲望;其二,接纳柏拉图把理性欲望解释成欲望主体对欲望对象的“缺乏”的这种做法,在各自的哲学视域内追求关于理念和理念知识的“智慧”。
“缺乏”由此变成了理性欲望挥之不去的梦魇,固化为理性哲学的内生性和结构性的驱力。尽管这种“缺乏”性质和它可能或不可能被克服的方式随思想家的不同而不同,但毋庸讳言,它在诸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的理论中都是一个支配性的组织原则。
柏拉图哲学的直接继承者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承接了柏拉图哲学的爱欲指向,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解。如同柏拉图的理性的欲望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视爱欲为“总的说是意向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分有理性”,“受理性的约束”。这种必须与理性相结合的爱欲是“有目的的”,而达此目的的手段则依靠考虑和选择。如此,爱欲对象变成了“可欲”对象,变成了“我们经过考虑力所能及的期求”。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代宗师的强力奠基,欲望的“缺乏”特性就此固定下来,已然构成了它的内生性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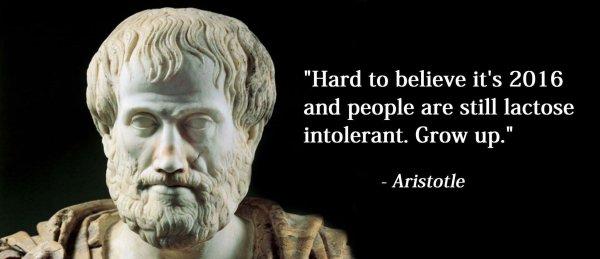
那么,作为爱欲对象的智慧又当如何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一方面,这一理解使“智慧”与身体之“感觉”脱钩,使灵魂所把握的作为知识和真理的智慧与身体所体验到的感性的意见相对立。智慧于是有别于人们日常所说的“聪明”,因为日常所说的“聪明”往往指的是感觉上的“耳聪目明”,而这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包括西方哲学史上绝大多数理性哲学家)极为鄙夷之事:“感觉是人皆尽有的,从而是容易的,算不得智慧。” 另一方面,这一理解又使“智慧”与“科学”相联系。感觉虽“算不得智慧”,但在智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正如康德所言:“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都是来源于经验的。然而,感觉虽然是智慧的经验来源,但其本身并不是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与由感性而来的意见(黑格尔称之为“感性确定性”)相反,智慧是关乎依靠理性才能求取的“本原” (本质、本体)和“原因”的知识。一切通过探寻事物的本质和原因而得来的知识,皆共享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智慧之名,在各自的领域深入事物的内在求经问道。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明确表达了哲学家对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智慧怀着一种挚爱的情愫。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对智慧的性质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智慧。”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指的“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而“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则指的是哲学。自然科学之智慧具有功利性,是“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就凸显了自然科学的这种实用性质。哲学之智慧则不然。作为诸科学之一,哲学不以实用为目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只为自身而存在,是一种为爱欲智慧而建立的自由的科学。
哲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诸智慧中享有高贵的地位。自然科学依靠知性(理智)探寻个别自然事物的个别和一般原因,其结论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的方法予以验证;而哲学依靠理性探寻具有最高层次的普遍性的、关于事物全体和整体世界的本原和原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始因”),即其他事物通过它们或由于它们而被知道的最初原因或第一原因。这种智慧具有理性思辨的性质,为经验证实力所不逮,其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经验证实的方法只能证实个别,不能证实一般乃至整体,因而不适合用于哲学。始因是全部事物和整体世界的始因,其本身就具有观念和思辨的性质,对于它的寻求只能通过观念推论和理性思辨的方式进行。这种用观念推论和理性思辨的方式追寻全部事物和整体世界的始因的学科,虑及事物的整体存在及其存在之根,亚里士多德之后又被称为“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兼具“爱智慧”和“是智慧”于一身的哲学,宛如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是众神(众科学)之首;又如镶嵌在智慧王冠上的明珠,居于众智慧的高山之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大智慧。它通过对全体自然事物和(包括人的)整体世界进行形而上学的理论沉思,把捉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同时又是他物的原因的“自因”(实体),统摄人安身立命的世界由之出又向之归的本原和基质,开显他物依之和由之而产生或存在的“始因”,进而向自然和社会颁布立足于人自身的精神法则和道德律令。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智慧、境界和胆魄。

黑格尔作为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顶峰和完成者,同样亦步亦趋地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爱欲路线上。黑格尔曾这样描述他写作《精神现象学》的目的,“正就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显然,黑格尔哲学的目标,并未脱离柏拉图所定下的爱智慧的主基调。
那么,哲学如何去爱智慧呢?黑格尔给出了一个爱欲智慧的自我,这个自我既是实体又是主体。自我所爱之智慧,是“真实的东西”,亦即自我认识了的“真理”。自我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它从认识物出发,进而认识到物的本质是自我,从而完成物和我的统一。在解决了物我之间的对立统一之后,自我又认识到有他者存在,他者事实上是另一个自我,从而完成自我与他者的统一。认识到他者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认识到社会的存在。自我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在伦理维度中实现了与家庭、社会的统一。在最后阶段,自我认识到有一个无限实体的存在,认识到这个无限实体即自我自身,自我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即“绝对”,从而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认识和与自己的统一。至此,“自我认识了绝对,也即最终认识了自己” 。
很显然,在黑格尔眼中,自我爱欲的真理,即为自我认识的真理,“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这种自我认识的真理,是一部意识以欲望为向导的自我的经验史,“意识所知道和理解的,不外乎是它的经验里的东西;因为意识经验里的东西只是精神的实体,即只是作为经验的自我的对象。但精神所以变成了对象,因为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如此,自我的欲望不是肉欲,而是“同化(欲望的)对象、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使之成为自己本身的欲望”。有鉴于此,法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科耶夫直言作为“黑格尔哲学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欲望哲学著作——感觉是“非个人的欲望”;知觉是“承认的欲望”;知性是“自由的欲望”。
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运动是欲望客体不断变换的运动。“绝对主体”犹如一员“经历磨难、耐得住人生一切矛盾、冲突而取得最终胜利的战将”,在不断地追逐着新客体、不断用一个新的客体取代另一个丧失的客体之后,最终带着“遍体鳞伤”达到了“绝对知识”的自我。对主体而言,意识新客体的每一次获得都是对前一客体的克服,每一种新客体的获得只有通过以前客体的死亡才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精神的生活才能在客体的不断死亡和更替中浴火重生,在自身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赢得自身绝对的真实和完满。

现代西方哲学巨擘海德格尔虽然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宣告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倡导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生存论,但他所阐发的此在的超越论和死亡哲学同样沿袭了柏拉图的理性欲望观。在他看来,此在是能够提出存在问题、追问存在意义的存在者,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哲学的任务是重提“存在问题”,建立关于此在基础分析的“基础存在论”,廓清存在的意义,以“保障一种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和“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故此,哲学必须以时间性为视野“解构”存在论传统,用存在论生存论对存在意义的爱欲取代传统存在论对存在者的爱欲。
同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也十分重视此在的意向性问题,把意向性视为此在的本质结构,指出“此在本质上就包括:存在在世界之中。”然而,与胡塞尔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意向性结构旨在说明的不是意识(主体)的一种先验性质,而是此在的反主体主义指向,这就使他的爱欲学说表现出不同于柏拉图爱欲路线的可贵之处和革命性改变。此在本身就是意向性的,即爱欲性的。在此在的这种爱欲结构中,无所谓爱欲主体与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世界只是此在的存在性质。此在是爱欲本身,它是向着世界的存在者,一向滞留于已被揭示的、前来照面的世内存在者,“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
然而,当论及如何从存在论上把握和规定此在的整体存在的可能性问题时,海德格尔又回复到了柏拉图的爱欲路线。在他看来,此在的存在具有超越性,它不断地超越自身、出离自身和先行于自身,因此,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作为能在的尚未变成现实的东西亏欠着,此在存在的基本建构就是一种持续的未封闭状态。此在存在的这种不完整性意味着在能在那里的亏欠,意味着“只要此在存在,在此在中就有某种它所能是、所将是的东西亏欠着”。由于这种“亏欠”的存在,把握此在的整体存在的可能性就不能像把握其他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一样等待着它的死亡(终结),因为“一旦此在全然不再有任何亏欠,一旦此在以这种方式‘生存’,那它也已经一起变成了‘不再在此’。提尽存在的亏欠等于说消灭了它的存在”。只要此在作为存在者存在着,它就不会达到它的“整全”。
要想从整体上把握此在存在的“整全”,就必须从存在论层次上而不是从存在者层次上来把握此在的死亡。从存在论生存论层次上看,死亡是“悬临”于此在存在之上的可能性,死亡“这一属于能在亦即属于生存的终结界定着、规定着此在的向来就可能的整体性”。因此,生存论上的死亡概念,是“向终结存在”,“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始终已经是它的尚未,同样,它也总已经是它的终结。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这样,通过对向终结存在的生存论结构的界说,海德格尔就向我们展示了此在能整体地作为此在存在的存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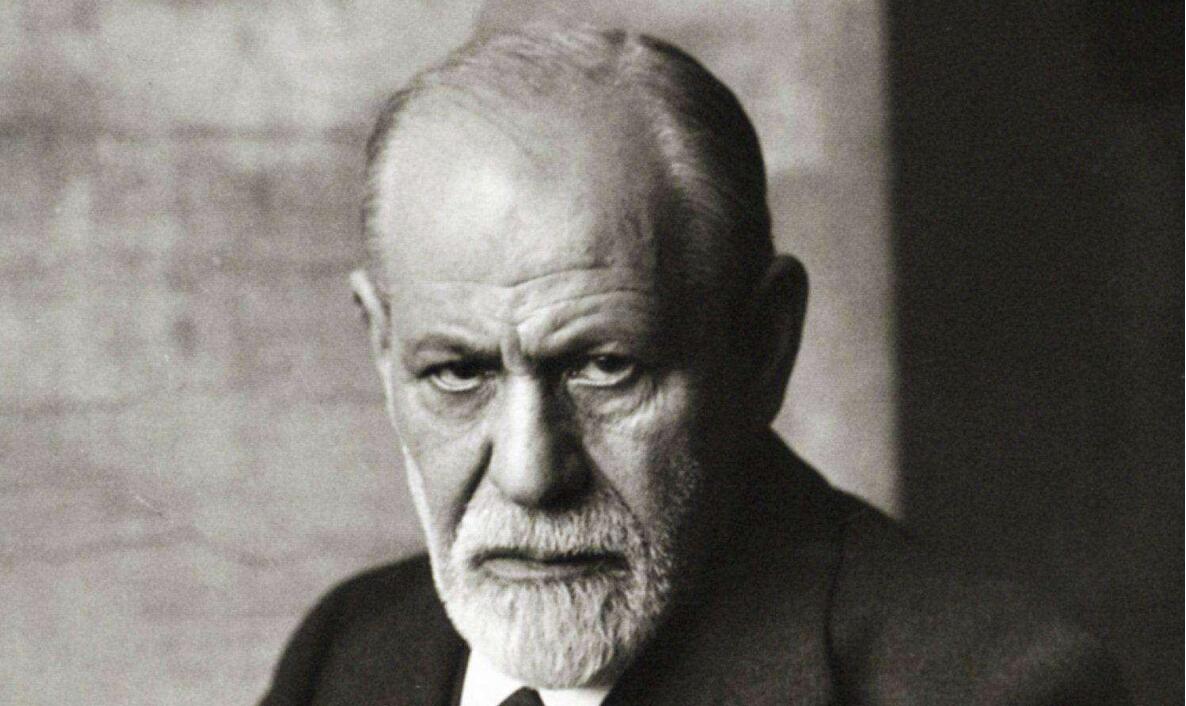
对观海德格尔和黑格尔,他们都预设了一个欲望所追求克服的结构性的缺乏。这种克服结构性缺乏的尝试和努力,可以分别被归入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哀悼”与“抑郁症”的范畴。对弗洛伊德来说,哀悼与抑郁症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异在于对象丧失之后的地位。就哀悼而言,丧失对象得到哀悼之后被另一个对象取代,“哀悼活动是力比多投资从一个对象转移的痛苦过程,为的是使它们能够被自由地附着于另一个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似乎被撤回和被抑制”。而就抑郁症而言,“在抑郁症中,丧失对象不被取代;它被等同于自我。哀悼活动不能完成,因为正常情况下派发为自由于其他投资的力比多投资向内转而附着于自我本身。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自我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某个东西,但这种知识不能变成意识,因为上述的投注仍然在运转着”。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所塑造的这种自我落入了一个被弗洛伊德称为“哀悼”(mourning)的精神陷阱中。在这里,意识的对象在否定的作用下不停地转换,这种转换过程横贯整个意识教育,并且首先根据“天启宗教”的内容,而后根据“绝对认识”的形式得到完成。否定的过程是肯定的否定,不是绝对的否定,每一个阶段都被随后的阶段占有和保存。每一次意识对象的被否定所唤起的都是一种类似于死亡的体验,但不是死亡的样式,因为没有绝对的丧失之点。如此,意识内部的地形学以哀悼为中心组织起来。在哀悼的过程中,意识把力比多投资从那个丧失了的对象上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用一个新的对象取代原来那个丧失了的对象。整个意识的发展过程是哀悼不停地运作的过程,也是意识不断地重塑自身的过程,黑格尔称之为知性的“绝对的势力”的劳作。
从精神分析学的解释者亚伯拉罕和图洛克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欲望观是对死亡的“内摄”(introjection),而海德格尔的欲望观则是对死亡的“吞并”(incorporation)。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相对于经验而言扮演着一个先验的角色。此在的存在既是时间性的——有死的和有限的,同时又是空间性的——临死的(dying),此在的世界就是围绕着它的“向死之在”(being towards death)组织起来的。此在所有的外在关系都只是它与自己的内在关系的一个功能,它在自己的界限之内与自己的个体化关系给予了它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即由于“向死之在”的体验而失去了世界对象,并由于失去了世界对象转而与自己发生关系,倾注于对象之上的力比多投资回撤进自我,把自我幻想成失去了的世界对象,最终自我“吞并”了自我(不像黑格尔那样以一个新的对象取代失去了的对象)。在这里,此在对于所失去的世界对象始终耿耿于怀,不肯放弃,它总是幻想着失去了的世界对象仍然存在,于是在其自我中就形成了一个藏有失去的世界对象的“窖室”(crypt)。在形成“窖室”这一病灶的过程中,此在的经验以此在的自我“吞并”自己的形式得到了重组,好像失去的对象并没有失去,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的“非本真的存在”。畏向此在把已经吞并了自身的自我揭示为它存在的中心。这是一种先验的抑郁症的症状。
由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把否定作为意识发展的引擎的欲望观基本上是哀悼的,而海德格尔眼中此在追求整全存在的“向死之在”的欲望观基本上是抑郁症的。这两种精神病症产生的根源,乃在于从根本上继承了自柏拉图以降把欲望视为缺失的思想路线。鉴于这一教训,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分辨和阐明了一条包括诸如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谟、尼采、柏格森、克罗索斯基(Klossowski),当然也包括第一个告知这一选择性的哲学史的德勒兹自己的欲望路线。这条欲望路线重新拾起的,不是源于柏拉图又为其后世哲学所倡导的灵魂(理性)欲望观,而是遭到柏拉图及其后世哲学贬抑的身体欲望观。就德勒兹而言,这种身体欲望观既不包含缺乏的结构,也不追求克服缺乏。身体欲望犹如一台“欲望机器”,自身就是物质性的、生产性的、肯定性的和积极性的,不断地生产、创造出新的欲望形式和新的欲望连接。身体不是主体,其所产生的欲望也不会因为缺乏而趋向客体,相反,它游离于欲望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欲望不缺少任何事物:它不缺少客体。相反,欲望中缺少的恰恰是主体,或缺少固定主体的欲望;没有压抑就没有固定的主体”。
毫无疑问,德勒兹把欲望看作生产性的、欲望并不围绕着一种结构性的缺乏来组织自己的这种身体欲望观,是对柏拉图爱欲哲学的彻底颠覆,也是对自柏拉图肇始的理性欲望路线的根本反转。
欢迎加入 弗洛伊德 · 荣格交流群 | qq群号:1020258170
本文精摘自《哲学分析》,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