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2-0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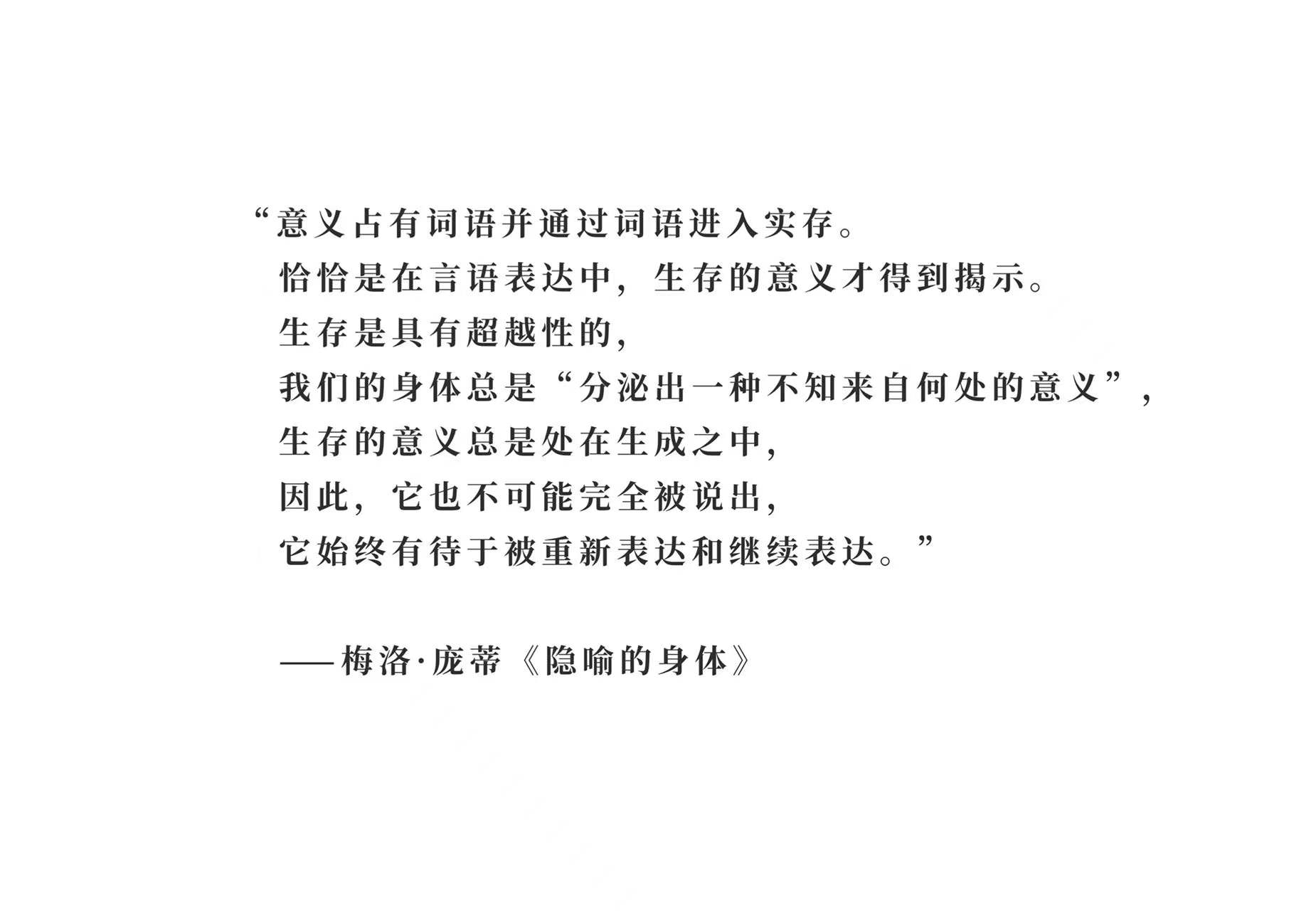
《逻辑哲学论》这本书是为思维的表达划定一条界线,世界是我的世界,表现在语言的界限指示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一事实之中。形而上主体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唯我论所意指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能说,它只能显示出来。
作为人的思维工具的语言本身,固然能够描述和塑造世界。但是,恰恰在对世界的描述和塑造中,它也遇到了其局限性。我们站在“界限”的这一侧,思考,用语言表述。因为作为形而上学主体的我们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界限”,所以世界作为有限的整体的感觉才会产生。
这个逻辑形式就是“界限”,因为它虽然使描述成为可能,但是它自身却不能再被描述。在其中出现了一些超越现实之外的东西。只有当在逻辑形式中展现出一些我们无法思考的东西时,它才是超越现实之外的,因为它是无法思考的,所以它就不能被说出来。
语言与形式都是呈现概念上的常规,而不完全是创意的表现。语言是人类最深的印记和标识,同时也是人最大的创造和负累,它涉及到有关人的基本问题的信念。由语言产生的人类思维能力,比任何其它东西更能够使我们融入身外的世界。
甚至,我们的自我也是通过语言的获得而实现的。语言是我们的所有的人性与个性的基础。所以语言也有了广义的性质,它所指的就是“符号”,而人正是“符号”的动物。
语言帮助我们创造了我们体验世界的范畴,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体验世界的,而语言又帮助我们形成了经验本身。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语言在每一点上都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相渗透。
而真正的创意和智慧是高于语言表达的。一个表达,只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 。怀疑论是不可驳倒的,但显然是无意义的,它试图在不能提问的地方提出怀疑。
我有一个世界图景。它是真是假?重要的是,它是我的一切探究和断言的地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的着力之处,便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
日常用语是人的机体的一部分,而也像是机体那样复杂。能显示出来的东西,不能说出来。一个形式概念是随着属于它的任何一个对象的给定而立即给定。真的思想的总体就是一幅世界的图像,情况可以被描述,但是不能命名。
我们的语言最初描述的是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有什么用处,怎样使用它,这仍然是不清楚的。然而,清楚的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的话语的意思,那就必须研究这幅图画。
言语作为身势动作的一种扩张,它也就和身体动作一样与身体的整体机能密切相关。意义占有词语并通过词语进入实存。恰恰是在言语表达中,生存的意义才得到揭示。离开了这种表达,意义要么处于沉默或沉睡状态中,要么即使存在,它也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
而言语表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表达从来就不是完整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生存本身是有限的;其次,生存又总是超越性的,我们的身体总是“分泌出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意义”,生存的意义总是处在生成之中,因此,它也不可能完全被说出,它始终有待于被重新表达和继续表达。
主体不属于世界,反之他是世界的界限。说话的主体在不世界之内,世界是可说的,但是主体不可说。说话的主体永远不能表达、分析言中的主体。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到外物,但却不能看到自己的五官。
即使把一切一切的总和称作世界,世界仍然不是一切,因为世界仍然需要一个背景才能呈现,我们说到世界仍然有所隐含。但这个“世界之外的存在”不是与“世界之内的存在”平级的存在。
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必须说很多话,然后回归于沉默。
沉默的意义在于它不断地聚集力量以溢出沉默的范畴。沉默并不是话语的绝对终结,它伴随话语而存在,是相对于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它构成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一部分,又渗透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中。
当苏格拉底提出一个问题时,首先蕴含着对具体蕴含的排除,因而,他一再地让人们离开具体的状态,这其实是在表明,我们谈论的不是具体形相,面对着它们,得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说,不是只有一种“语言逻辑”,而是有许多种“语言逻辑”;语言不具有单一的本质,而是由各有其自身逻辑的实践组成的广大集合。意义并不存在于字词与事物之间的指示关系或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图示关系。
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类其他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我们在场景中学会说话,在场景中理解语句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语句逐步脱离特定的场景,话语套着话语,一个词的意义由另一个词或一串词来解释。若把语言视作一个大领域,有一个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就是语言游戏。
当我说“痛”这个词,并没有指代任何一种可以被他人完完全全接收理解到的客体,语言在这里只是作为“疼痛”这个动作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有什么理由把“E”称为一种感觉的记号?因为“感觉”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的词,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懂的语言中的词。所以这个词的使用需要有一种人人都懂的辩白。——下面这种说法也并没有什么帮助:“E"不一定要是一种感觉;在他写下“E”时,他有某种东西——而这就是所能说的一切。但是“有”和“某种东西”也属于我们的共同语言。
这样,当一个人在从事哲学时,最后就会走到这一步:他想仅仅发出一种不甚清楚的声音。但是这样一种声音,只有当它处于一个现在就应加以描述的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时才成为一个表达。
如果把“E”解释为“不能通过语言展现”的“直接经验的事实”的特定的词语的话,维特根斯坦就会认为:“直接经验的事实”这一话语也是我们共通(可以互相被理解)的话语,所以这一话语一直都置身于特定的语言游戏之中了。如果拒绝承认这一点的话,“E”就只是语义不明的音节而已。
体验能够独立于语言的记述而拥有某种含义,语义也不过是一种体验罢了。纯粹经验自身存在于使语言成为可能的内部构造之中,“暧昧不明的音节”能够成为一种语言表达并不是因为外部的“语言游戏”给予其语义。而是从内部的将这些音节赋予含义的力量和构造,自身就存在于经验之中。
他人和我是通过音和形之类的物体现象的手段实现相互理解的。其中“音和形”也就是符号。然而用符号这一手段仍然未能理解这一难题:为何未直接结合的我和他者能够相互理解?
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类,都可以认为是“在我之内”,而只有你不能认为是“在我之内”,而应是“对我来说的无”。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包括你我的普遍存在物。然而即使如此,限定我的只有你,我只有承认了你的同时我才能成为我。不过,“我对你的承认”不过是“在我自身内部”所实现的,在“我自身内部”可以认为有一种“非连续的连续”,共同限定了我和你的同一原理(具体来说是语言)也能够在那里存在。
我和你的相遇,就是在我自身的内部将我自己绝对的否定(杀死自己),正因为如此,我诞生了。我被你所杀死,是因为你在我之中是无,而我在你之中则是有。
在和你相遇之前,我只是一个场所,还什么都没有,也可以成为任何东西。我是无的场所,所能存置的是全部的存在物(有),然而你并不是存在物,在我的无中仍然是无,我和你无法直接相遇。可以直接相遇的,是他和他(两个个体存在者)。我只要作为个体存在者就可以和作为个体存在者的你相遇,只不过我和你都是场所(无),所以绝不可能相遇。在我的角度看来,你的场所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甚至连无的场所都没有出现,连无都称不上,所以称作比无更甚的虚无。然而你为什么有作为另外一个无的场所的资格,在我的无的场所中登场了呢?因为你是可以用语言言说的存在,或者更正确地说,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东西正是语言(被语言所描述的新种类的场所)成立自身。
如果这(在我的无中你的登场,也就是你我相遇)成为可能,我就不仅是无的场所,更进而是另一个无的场所中的一个存在者(有)了。那时,你就像是存在于我内部的作为绝对无的上帝一样,“不论何处都作用在我的内部”,自此我的内部,就有了一个像上帝一样,使我成为我的另一个无。
上帝就是概念化之前的实存。我成为了主格,一个自我。如此一来,我就不再是无的场所,而是在另一个无的场所之中登场的存在者(有)之一。这是我的死亡,也是我的诞生。因为在他者的无的场所中登场,我在我自己的(原生的)无的场所中,作为一个人(个人)或者是拥有固有名的个体而登场了。
在这时,我和你都成为了第三者“the third person=第三人称”的他的场所,一个抽象客观的场所从此诞生。于此,“无的场所”就可以作为“无的场所”这一普遍化的词语来表达,而我也从此可以用“我”这个词语来把握我自己了。也就是说我也可以将我,用“我”这种再归的/反省的方式来加以把握了。
至于维特根斯坦的“E”为何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的个别存在者,也有了答案。因为概念的场所已经是客观化的了。“感觉”虽然是私密的事件,然而这不过是被“感觉”这一场所客观的确保之后的私密性而已了。你我都可以共有感觉的概念。
而由于我的作为绝对无的存在方式被否定,变得能够在个体存在者关系之间来把握自己,所以不得不同时也否定掉自己作为与格(场所)的存在方式,而将我把握为主格。而我也无法再返回无了。
